小巷人家陈从周原文(小巷人家阅读全部答案)
小巷人家陈从周原文(小巷人家阅读全部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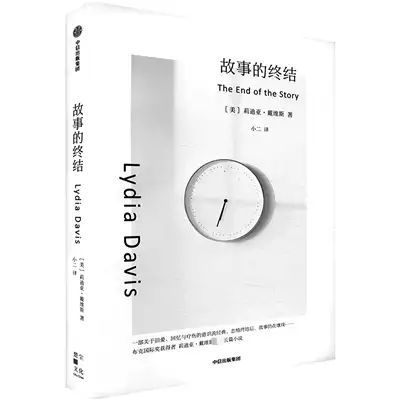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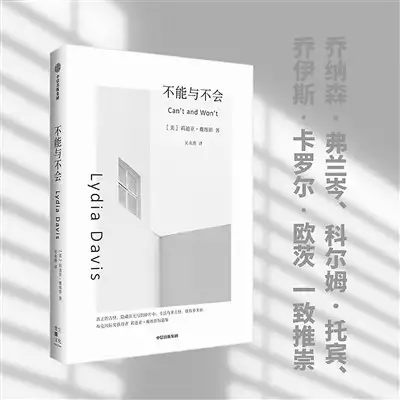
◎三心
作为译者,莉迪亚·戴维斯翻译过《追忆逝水年华》与《包法利夫人》等文学作品的英文新译本,而作为作者,她在短篇小说领域又开拓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莉迪亚·戴维斯的句子有福克纳长句章法的印记,但摒弃了那身陷迷阵的效果,用词更简洁、意义更明晰;她吸收布朗肖迷人的悖论结构,但弃绝了那晦涩难溶的哲思,掉头到生活化、内心化的轨道;她放大普鲁斯特关于意识和情感的光晕,但在篇幅上大幅度缩减;她的一些短篇在风格上形似罗兰·巴特,但叙述的传统依旧存在——虽然这叙述只残存了星星点点。
将小说作为容器
对于莉迪亚·戴维斯而言,短篇小说像是一个和善的容器,可以慷慨地容纳形形色色的形式。她的一些小说很难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更像是某种散文,但归类于散文又似乎无法准确把握她的奇妙风格。在写作形式上莉迪亚·戴维斯的小说与加莱亚诺的《拥抱之书》相近,但前者更包罗万象,也更激进深刻。一些小说甚至蕴含了现代诗的质感,甚至有时会像诗歌一样进行分行。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她的小说像很多人但又不像任何人,成就的是独一无二的莉迪亚·戴维斯。
故事在她的小说中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显影,通常在较长的短篇中故事以走马观花的片段形式奔驰而过,缺少细节的描写和必要的逻辑,如同列车飞驰般诉述人物的一生或者只是人物思想絮语片段的合集。吊诡的是,越是复杂迷离的句子在意义上越透明,而那些用简单朴素的语言散漫推进的故事却显得困惑难解。
在她较短篇幅的小说中,别的作家推到舞台中心的故事在莉迪亚·戴维斯的笔下成了幕布。她在故事的某一个节点停顿,然后深入肌理,穿透内心,层层剖析,沉潜入人物的深处,表达的方式是莉迪亚·戴维斯式的——流连于词语的切割与分解,直至词语粉碎,让意义的内核涌出。某种意义上,这种翻来覆去折腾文字的方式接近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她善于使用转折的手法——“或者更准确地说”“又或者说”——去迈进更深层次的现实。在一次又一次的分裂中,我们会得到完全有悖于常理的结论,但往往这种结论更接近于我们感受的真相。
莉迪亚·戴维斯的文字极为精巧,她敏锐的目光可以通过某种简短的意象,辅以形容词,揭露出生活的本质。通常可以从一个作家的比喻窥见文字之美妙——《监狱娱乐室里的猫》中那残忍而形象的比喻“猫像下雨般从屋顶落到他身上”,隐晦地传递了猫和人似乎同一命运的暗示;她也会在比喻中运用通感的技巧“他感觉寒冷像一把钳子一样夹住了他”;《卡夫卡做晚餐》中形容城市“好像是一个墓园,我的心里是那么安宁”。看似在我们心中造成截然相反印象的喻依和喻体被嫁接在一起,比如她形容美好时光快速增加就像老鼠——边界被消解,激发了一种电流般的效果。
在创作的中后期,她小说的概念也越来越体现在标题和内容的张力上,甚至只有通过标题才能更好地理解小说,标题晨星般照亮了小说文字令人迷茫的道路。小说可能只是由短短几句话甚至就是一句话组构而成,让人感到扑朔迷离。如果忽略标题,那么就完全无法理解小说内容的表达。像《塞缪尔·约翰逊很愤慨》仅仅只有一句话:“苏格兰的树那么少。”
莉迪亚·戴维斯是善于运用比较的大师,她别出心裁地在天秤两端放置相似的概念,在这种比较之下曝光了诡异的事实——日常使用的概念或思想往往是不那么贴近事实,甚至是背离事实的,而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形状或变换说法后反倒离奇地透视到真相。在《双重否定》中就进行了这样一个对比:“想要一个孩子”和双重否定的说法“不想不要孩子”。显然“不想不要孩子”更真实,也更冰冷,“想要一个孩子”中作为主语的她是生活的主动者,有着自己的自我意志,而在“不想不要孩子”中,似乎隐约派生了这么一层意思,她不再主动,而是被动的,在这里真正主导她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例如社会规范、生活条件、传统思想等等,作者将其隐匿在幕布后用胶布封存,透过比较的力度,一种沉痛而残酷的“真”反射到读者的思想中。
把平凡写得有趣
莉迪亚·戴维斯有着将平凡事情写得极度有趣的能力。《独自吃鱼》中仅仅是吃鱼这样平凡的行为都需要经过许多的心理挣扎。我们在意别人的看法,懊悔于自己细微但无法补救的行为,一件日常的琐事可以在人物心里涌起巨大的风暴。
在《我的一个朋友》朴实无华的开端“我正想着我的一个朋友”之后漫散开思绪的涟漪,在词语的自我新陈代谢中蜕变出一种超越庸常的真实,随即回荡到自身,一个突如其来的转折“我突然想到我肯定也不完全知道我自己是谁”,小说的某个本质性在其中泛光——每篇小说指向的必然是读者自身。在莉迪亚·戴维斯小说中会经常出现分岔,在一个行为上进行拓宽、延展——“还不如说是在等,并且经常,就像现在,感觉自己在等待”。因为人物在做一种行为的时候不单单只是做这一种行为,这只是种简单的“以为”,实际上人物的状态要复杂得多。
复杂与孤独往往是孪生兄弟,莉迪亚·戴维斯小说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无可避免是孤独的,他们不理解别人,同样也不为别人所理解。莉迪亚·戴维斯捕捉到人内心深处最细微的变质与腐烂,生活如此贫乏,甚至于连我们对生活的幻想也如此贫乏。小说要做的就是直面这种贫乏,但因为小说的突触连接到了这种贫乏的实质,因此小说不再贫乏,而绽放出了炫目的光华,即使这光华的养分是生活的幽暗。
在《一个老女人会穿什么》中,时间性被彻底肢解,在不断的斧凿中,最初的梦想被夷为平地——我们到了一定年龄后会享用自由——这种梦想的虚弱性袒露无遗,“虽然她知道,在那个时候来临之时,一顶帽子和随便戴帽子的自由将无法补偿变老让她失去的其他所有东西”,而更进一步“或许说到底,即便仅仅是想想这种自由都没什么可高兴的”。
《背叛》是莉迪亚·戴维斯最为沉重的短篇小说之一,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小说中的“她”对其他男人的幻想程度随着年月逐渐降低,到最后“这种幻想变得与她清醒时的现实没有差别了”,如此地步之时,幻想还是背叛吗?但这种平庸的幻想依然是某种背叛,因为幻想是出于某种背叛情绪而产生的。人们被困在某种微妙的悖论里:因为背叛而幻想,而幻想中没有任何背叛,这是无法解开的死结。在《她过去的一个男人》中,莉迪亚·戴维斯再次探寻了背叛这一概念,过去和现在被混淆在一起,以至于母亲的儿子产生了这样的困惑:尽管她的身体衰老了,但她背叛的能力却依然年轻而鲜活。
对生活微妙的感悟
在她的第三本短篇小说集《不能与不会》中,我们能清楚地感知到字里行间对生活感悟的微妙变化。在创作形式上,开始更加自我,更加信马由缰,她可以将改稿过程都跃然于纸上,甚至连作家本人的名字都出现在了小说中。同时小说之间的联结性更强了。她利用相同的形式和副标题创作了多篇藕断丝连的小说,如福楼拜的故事、信,以及梦,并将它们在小说集的群岛中打散分布。
每个系列中的小说都有着相同的灵感来源,比如“梦”系列就源自于自己和不同朋友对她诉说的梦的内容,当然梦所展示的形式也必然被加以改造。她同样对所谓的梦进行了反方向微妙的讽刺。在这里,小说的虚构性似乎被再次披上了一层光晕。小说是虚构的,而这部虚构性的小说所讲述的是梦的虚构性,于是这些小说有了双层虚构。人物提供了一些文本,这些文本可以从潜意识角度进行解读,但同样可以仅仅让读者去激赏那天马行空却又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超现实描绘。
在以前的作品中,莉迪亚·戴维斯可以通过几个瞬间去映照一个人的人生,仿佛漫长岁月可以被浓缩在短短几页纸上。在《她的破坏》中,仅仅通过生活上各种琐碎事情的失败就仿佛概括了一生的失败。在小说的结尾,她为孩子拍照片然而相机里却忘了放胶卷,充满了伤感,就好像她这一生没有什么真正值得记录与留存,也许真正美丽的瞬间只存在于她的想象中。而在这部小说集中,生活的哀叹转为对死亡的慨叹,有许多对于死亡之体悟的小说矿藏,虽然都是短篇,但可以感觉到时间让她的沉淀越发厚实。技法上的一个转变是开始越发地强调视角,《火车的魔法》中与其说是火车的魔法,倒不如说是视角的魔法。当我们在背后看她们的时候,穿着姿态犹如少年,而当我们在迎面看她们的时候,她们的老态龙钟纤毫毕现。火车在这里似乎为时间赋形,在视角的变化下,时间流逝所带来的雪崩席卷而来。
在之前的作品《你从婴儿那里学到的东西》中,她教导我们从婴儿身上可以收获到更多,返璞归真,因为我们长大不是获得而是遗失。在这部小说集中,她强调即使在最平凡的事物中也能发现非同凡响的钻石般的光辉,这让这部小说集折射出一丝暖意。在其中最美的一篇小说就是《母牛》,通过描写几头牛的观察记录,如同雾一样慢慢弥漫开生活道理的领悟,或者某种零散零碎之美。平常的观察,但又使用了意想不到的新奇的观察角度,在表象中迸发了无可计数的美,而这种观察仿佛又可以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
- 上一篇:54岁梁实备战第25次高考(梁实从1983年到今年,已
- 下一篇:没有了
